探索自然之大峡谷蛇踪(一)
说起大峡谷,一副厚重的自然历史画卷便在我的脑海中徐徐展开:山水勾勒的每一笔色彩,脚步丈量的每一寸土地,亦如初遇那般让人迷醉,日久弥新。
2020年初夏,彼时广东燥热的气温已面目狰狞,临近大峡谷景区,轰鸣的瀑布声如雷霆万钧,给初来咋到的我来了个醍醐灌顶。瞬间,夏日的烦闷被腾龙的咆哮一扫而空,我迫不及待的想撞入它的怀里,一睹其绝伟身姿。于是,我们不自觉的加快了脚步,一路扯着脖子,生怕这条久负盛名的腾龙从我们的视线中飞走。终于,在经过“漫长”的5分钟的步行后,我们到达了第一个观景平台,映入眼帘的不是腾龙瀑布,而是“熊咆龙吟殷岩泉,栗深林兮惊层巅”的绝奇峡谷。我久久矗立,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中摇曳着心灵——对,我此刻正步入那玄乎其玄的“冥想”状态。“快看啊”,这突如其来的呼唤声打断了我的思绪,我如机械般顺着同伴的指尖聚焦着目光,只见两名身着华丽的杂技演员在峡谷上空辗转腾挪、上下翻飞。“云端起舞惊飞鸟,空中翻腾似游龙”,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折服。当然,大峡谷除了让人惊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,最让我心心念念的确是那隐匿于连绵群山中的动植物资源。
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里,我几乎踏足了大峡谷的每一个角落,发现大量峡谷地带性特色植物物种,如大果巴戟(Morinda cochinchinensis)、大齿马铃苣苔(Oreocharis magnidens)、大叶石上莲(Oreocharis benthamii)等,具有极高的物种及栖息地保护研究价值;记录到包括黄腹角雉(Tragopan caboti)、中华鬣羚(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)、福建柏(Fokienia hodginsii)、华南五针松(Pinus kwangtungensis)等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,表明峡谷片区物种的多样性、稀有性及典型性。
二、蕉窝里的篝火
当然,对于一个两爬爱好者来说,夜晚的探险才最让人着迷,但由于大峡谷保护区内交通条件有限,想在核心地带开展夜间调查,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时间回到2020年10月,在夏季充分踏查的基础上,我们一行人整装待发,向着蕉窝这个既定目标进军。迎着清晨的太阳,我们一个个基情满满,嗷嗷的往山顶上冲,我刚想感叹年轻就应该无所畏惧,勇往直前,就听到战友哀嚎的声音:“不行了,不行了,这山太陡了,咱休息下吧”。额好吧,帅不过3秒,这注定是条炼狱之路,祝我们好运。漫漫“行军路”
“上帝视角”下的蕉窝
在我们一路自嘲,晃晃悠悠的畅想山顶的康庄大道的时候,突然从旁边灌丛窜出了一条满身横纹的翠青蛇(Cyclophiops major)宝宝,顿时激起了大家的兴趣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讨论着这条奇特造型的小蛇,一度有队员嘀咕道:“说不定是条横纹翠青蛇(Cyclophiops multicinctus)呢”,一顿疯狂的影像输出后,我们又开始了机械性的行军之路。翠青蛇(Cyclophiops major)
垂直爬升近300m后,我们终于抵达了脑海中的那条康庄大道。山顶特殊的灌草生境,虽然风景独特,但因水源匮乏,适宜两栖爬行动物栖息的小生境较少,一路只偶遇了几条耐旱的草蜥,也算是给这枯寂的赶路旅程泛起一丝涟漪。山顶的康庄大道
北草蜥(Takydromus septentrionalis)
古氏草蜥(Takydromus kuehnei)
虽然赶路前就知道到山顶的荒凉,但长时间的零发现加上秋老虎的炙烤,我们的身心已经疲惫不堪,渴望森林小路,渴望涓涓细流,更渴望目标物种的闪现。终于,在漫长的急行军后,我们抵达了这一战的隘口。大家迫不及待的钻进了这个形如口袋的山坳,体验了一把“速降”的激情。据不完全统计,接下来的3个小时我们先后使用了“四肢并用法”“匍匐前进法”“臀式下山法”等各式新奇的方法,完成了高差达400m的下山旅程。隘口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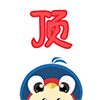



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0760号
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0760号


